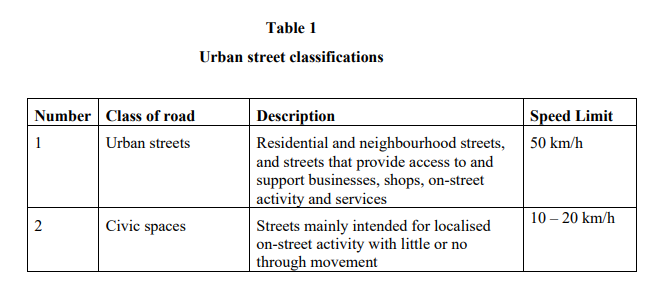在Reddit 上看到过不少岛国现右翼政府提供的“高效率”版本,疑似食物的学校午餐,但这玩意儿已经被讨论无数回了,似乎自己也没什么可以补充的。如果有人告诉我,我正在吃的正餐只花了不到三块钱,而且这还包括冷链物流成本以及供应商的利润,我敢不敢下口可能都是个问题。这个成本,哪怕是成本最低的土豆泥都必然不会是新鲜的,而是那种泡水的土豆泥粉。
可能最长相和成本靠近的是飞机上的cattle class 餐食,不过飞机餐供应商不用供应全国每一个角落。
我当然知道支持经济专家党的人会说什么 —— 午餐是个人责任,政府不应该负责,或者‘有得吃就不错了,还不感恩”。如果就是坚持意识形态大于一切,给炒房客减税比学生午餐重要,那是个人信仰自由,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—— 按此逻辑,学生出勤, 或者自家的土地上能建多少以及多高的房子都是个人自由,不知道“小政府”的Seymour 会怎么看。
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学校午餐被“高效”化之前,政客的说法略微有些不同:
- “学生们将会收到他们愿意吃的营养食品。这些食品就和家长们每天为孩子准备的午餐一样 —— 三明治和水果。”
- “我们刚刚为您节省了 1.07 亿元的学校午餐费用 …… 我们将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,让孩子们吃他们父母会吃的水果和三明治,而不是寿司等’woke food’”。
等等,说好的“水果和三明治”呢?那么多照片里我是没有看到过哪怕一次。当时承诺的可是用更少的钱达到更好的效果,而不是“有得吃就不错了”。而且这可不是”左棍“,而是Seymour 自己说的。
bait & switch算是最古老的销售手法了,政客当然也是专家。而当今政治的一大问题就在于,人们沉迷于对抗,或者”owning the libs”,而专注力之外政客说了啥,输送了多少利益都没有人关心。这些话压根都不是历史记录,就是大半年前的事,而现在还有哪家岛媒记得Seymour 承诺过的水果嘛?从”左棍说我们不关心学生福祉,但你看我们做得更好更便宜”,到“这根本就不是政府责任”,话题已经成功被转移。
另外好奇搜索了一下监狱里都吃什么。照片上看上去都可以辨别原本形态的食物,惩教部网站上有每星期的菜单 —— 早饭有牛奶,中午有新鲜水果,看上去确实比学校好。